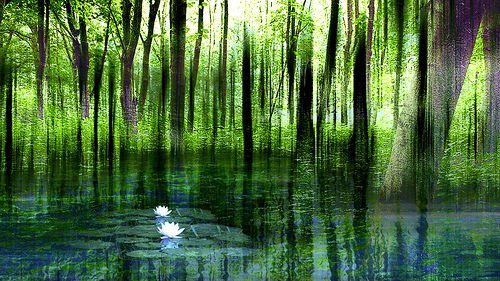第十二章 「不確定」——聖者的標準
曾有位西方比丘,是我的學生,每當他看見有泰國比丘與沙彌還俗時,
他就會說:「噢,真遺憾!他們為何要那麼做?
為何會有如此多泰國比丘與沙彌還俗?」
他很震驚。它對件事感到難過,因為他才剛進來與佛教接觸,
這激發他下定決心成為比丘,並心想自己永不還俗。
但過了一段時間,
有些西方比丘開始還俗,它也逐漸認為還俗並沒什麼大不了。
當人們受到激發時,一切似乎都是正確與美好的。
他們不會判斷自己的感覺,且並不真的瞭解修行,
卻繼續前進,形成一種主觀的看法。
而那些真正知道的人,心中都會有堅定不移的基礎——但不會吹噓。
厭煩清淨生活 便可能還俗
以我自己而已,當剛出家時,
實際上並未做很多修行,但我很有信心。
但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,也許是與生俱來的吧!
在雨安居結束時,和我一起去的比丘與沙彌都還俗了。
我心想:「這些人是怎麼了?」
但我不敢對他們說什麼,因為我還不確定自己的感覺,我太激動了。
但在內心深處,我覺得他們都很愚蠢,
「出家很困難,還俗卻很容易。這些傢伙沒有大福德。
他們認為世間的方式比『法』的方式更有用。」
我就是那麼想,但什麼都沒說,只是觀察我的心。
我看著和我同行的比丘們陸續還俗,有時他們會盛裝來到寺裡炫耀。
我看著他們,心想他們瘋了,但他們卻自認為看來很時髦。
我覺得他們錯了,但我沒說,
因我自己仍是個未定數,還不確定自己的信心能維持多久。
當我的朋友們全都還俗時,我斷絕一切關心,任何人的離開都與我無關。
我拿起《別解脫戒本》①研讀,埋首於其中。
不會再有人來煩我,並浪費我的時間,我專心于修行。
我還是什麼都沒說,因為覺得修行一輩子,也許七、八十甚至九十年,
一直維持精進不懈與不放逸,似乎是件非常困難的事。
會出家的人就會出家,會還俗的人就會還俗,
我冷眼旁觀一切,並不擔心自己會留下或離開。
我看著朋友們離開,但我心裡覺得這些人都未看清楚。
那西方比丘可能也是如此想,
他看到人們出家的時間只是一個雨安居,覺得很難過。
之後,他達到一個我能稱為……
「厭煩」的階段,對清淨的生活感到厭煩。
於是他放下了修行,最後還俗了。
「你為何要還俗?」我問他,「以前時,當你看到泰國比丘還俗,
你會說:『噢,真遺憾!多可悲,多可惜呀!』
現在,輪到你自己想要還俗,為何你現在不會覺得遺憾?」
他沒有回答,只是不好意思地咧嘴苦笑。
修心的困難 在於沒有衡量的標準
談到心的訓練,
若你心中沒有親自「見證」,要找到一個好的標準並不容易。
對於許多外在的事情,我們可以依賴別人的回饋。
但談到「法」的標準,它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嗎?
我們已有「法」了嗎?我們的想法正確嗎?
若它正確,我們能放下正確嗎?或仍執著於它?
這很重要,你們應持續思惟,直到能放下,
不執著好與壞為止,然後將這個也拋開。
換句話說,你們應拋開一切,若一切皆空,那就無有剩餘了。
因此,關於修心,我們有時可能會說它很簡單,
但說是容易,去做卻很難,非常困難,難在它違背我們的欲望。
有時事情有如神助,每件事都很好;無論想或說什麼,似乎都無往不利。
然後,我們便執著那個好;不久後開始做錯,一切便都轉壞了。
它就是難在這裡,沒有可供衡量的標準。
有人充滿信心,他們只有信而無慧,可能專精於定,但缺乏洞見。
他們只看到事情的一面,且完全照著走,不知省察。
這是盲目的信仰!在佛教中,這稱為「信勝解」(saddha adhimokkha),
有信心固然很好,但那產生不出智慧。
他們還不瞭解這點,而相信自己有智慧,因此看不到自己錯在哪裡。
依據「五力」 作為衡量修行狀態的標準
因此,經中教導「五力」(panca bala):
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。
「信」是深信;「精進」是勤勉的努力;
「念」是憶持;「定」是心的專注;「慧」是遍知的智慧。
別以為「慧」只是智慧,它是包含一切的圓滿智慧。
智者給了我們這五個項度,好讓我們可以檢視它們。
首先,是作為學習的對象;
其次,是作為衡量自己修行狀態的比較標準。
例如,「信」:我們是否確信,我們已發展出它了嗎?
「精進」:我們夠精進嗎?精進的方法正確嗎?
每個人都在精進,不過那是明智的嗎?
「念」的情況也是如此,即使貓也有正念。
當它看見老鼠時,就會有正念,眼睛會一直注視著老鼠。
眾生,包括動物、罪犯與聖者在內,都有正念。
「定」或心的專注,眾生也都有,在貓的正念中也有「定」。
至於「慧」,貓也有,不過那不是像人一樣的寬廣智慧,
那只是動物的覺知,它有足夠的「慧」能捕食老鼠。
這五項都被稱為「力」。這五力從正見中生起了嗎?
我們衡量正見的標準為何?我們必須清楚地瞭解這點。
依據正見 作為檢驗修行的標準
正見是對一切事物都是不確定的瞭解,因此佛陀和一切聖者們不會執著它們。
他們是「執」而不「著」,不會將執取變成固著。
一個不會演變成「有」的執,是不被貪欲污染的執,
不會尋求變成這個或那個,單純只是修行本身而已。
當你執著某件事時,事快樂或痛苦?
若是快樂,你執著那快樂嗎?若是痛苦,你執著那痛苦嗎?
有些見解可以拿來作為衡量修行更準確的原則。
例如,相信自己比別人好,或和別人相同,或比別人笨,這些都是邪見。
我們可能會覺得這樣,但也會以智慧加以覺知,覺知它們就只是生滅法。
認為我們比別人好是不正確的;
認為和別人一樣,也不正確;認為比別人差,也是不正確的。
正見能斬斷這一切。
若自認為比別人好,驕傲就會生起,它就在那裡,但我們卻沒看見。
若自認為和別人一樣,就不會在適當的時機表示尊敬與謙虛。
若自認為比別人差,就會意氣消沉,相信自己不如人,或是命不好等。
我們仍執著於五蘊,一切都只是「有」與「生」。
這是可用來衡量自己的標準。
另外一種是:若遇到愉悅的經驗,我們便感到快樂;
若遇到一個不好的經驗,便感到痛苦。
我們能將喜歡與討厭的事,都看成具有相同的價值嗎?
以此標準檢驗自己。在日常經驗中,當我們聽到某件喜歡或討厭的事情時,
心情會跟著改變嗎?或心根本不為所動呢?由此便可做個檢驗。
只要覺知你自己,這就是你的見證者,別在貪欲強烈時做下任何決定。
貪欲會讓我們自我膨脹,而想入非非,我們一定要很謹慎。
依據實相 作為覺知的正確方式
有許多角度與觀點需要考慮,不過,正確的方式並非跟隨貪欲,而是實相。
我們應同時覺知好與壞,覺知它們後,便放下。
若放不下,我們就還「存在」,我們仍然「有」,
我們仍然「是」,接著便會有後續的「有」與「生」。
因此佛陀說,只要評斷你自己,
不要評斷別人,無論他們可能有多好或多壞。
佛陀只是指出道路:「實相就是如此。」現在,我們的心是否如此呢?
例如,假設甲比丘拿了乙比丘的某些物品,乙比丘指控他:
「你偷了我的東西。」「我沒偷它們,我只是拿了它們。」
因此,我們請求丙比丘仲裁。他應如何決斷?
他必須要求犯戒比丘出席僧伽集會。「是的,我拿了,但並沒有偷。」
或衡量其他規定,如波羅夷罪或僧殘罪②:
「是的,我做了,但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你如何能相信他的話呢?那太難捉摸了。
若你無法相信它,就只能將罪過留給做者,它歸於他。
但你們應該知道,我們無法隱藏心中生起的事,
不論是錯誤的或好的行為,都無法掩蓋它們。
不論行為是善或惡,
都無法藉由不理會來打發,因為它們會自行揭發。
它們隱藏自己、揭發自己,
它們自顧自地存在,全都是自動的。事情就是如此運作。
不要試圖猜想或臆測這些事情,只要無明仍然存在,它們就不會結束。
有位議長曾問我:「隆波!『阿那含』的心清淨了嗎?」③
「它只是部分清淨。」
「咦?阿那含已斷除貪欲,心怎麼還未清淨呢?」
「他可能已放下貪欲,但還殘留一些東西,不是嗎?還有無明。
只要還有殘留,就是還有些東西存在。
就如比丘的缽,有大、中、小型的大缽,
還有大、中、小型的中缽,以及大、中、小型的小缽……
無論缽多小,它還是個缽,對嗎?
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等的情況也是如此,
他們都已斷除某些煩惱,但都只在各自的層面上。
至於還剩下什麼,那些聖者們看不見,若能看見,就都成為阿羅漢。
他們還看不見全部,所謂『無明』,就是沒有看見。
若阿那含的心已完全通達,就不會只是阿那含,他會成為正等正覺。
只可惜,還是剩下了某些東西。」
「這顆心淨化了嗎?」「嗯,只到某種程度,還不到百分之百。」
我還能怎麼回答呢?他說以後他會再來進一步問我。
你真的認為 修行有這麼簡單嗎?
別放逸,佛陀告訴我們要警覺。
在這修心的過程中,我也曾受過誘惑,
去嘗試很多事,但它們卻似乎總像是迷了路一樣。
它們是種浮誇的心態,一種自滿,
它們是「見」與「慢」,要覺知這兩件事真不簡單。
曾有人為了紀念母親而想出家,他抵達這間寺院,
放下衣服,甚至未禮敬比丘,就開始在大廳前行禪……,
來來回回,好像在炫耀一般。
我心想:「哦,也有像這樣的人!」這是盲信。
他一定已做了類似要在日落前覺悟的決定,大概認為這很容易。
他目中無人,只是埋首行禪,仿佛那就是生命的全部。
我什麼都沒說,只是讓他繼續做他的事,但我心想:
「喂!年輕人,你真的認為修行有這麼簡單嗎?」
我不知他後來待了多久,我甚至認為他沒有出家。
一旦心想到什麼事,我們每次都會將它傳送出去。
我們不瞭解這只是心習慣性的造作,
他會將自己偽裝成智慧,並在微小的細節上胡謅。
這個心的造作似乎很聰明,若未好好覺察,我們可能會將它誤認為智慧。
但到了關鍵時刻,卻不是這麼一回事。
當痛苦生起時,所謂的「智慧」在哪裡?
它有任何用處嗎?它根本就只是造作的假像。
從內心 找到佛陀
因此,請與佛陀同在吧!
在修行中,我們一定要轉向內心,找到佛陀。
佛陀至今天都還活著,去裡面將他找出來。
他在哪裡?就在無常中,進去裡面將他找出來,
去禮敬他——無常、不確定。你們可以從這裡開始。
若心試圖告訴你,你現在是須陀洹,
你就把這個想法交給佛陀,他會說:「一切都不確定。」
若你認為你是斯陀含,他只會說:「並不確定!」
若「我是阿那含」的想法生起,佛陀只會告訴你一件事:「不確定。」
甚至,當你自認為是阿羅漢時,它會更堅定地告訴你:「一切都『非常』不確定。」
這是聖者的話:「每件事都不確定,不要執著任何東西。」
別一味愚蠢地執著事物,別緊抓著它們不放。
看見事物的表像之後,便要超越它們。
你們一定要如此做,那裡必然是表像,也必然超越。
因此,我說:「去見佛陀!」佛在哪裡?佛就是「法」。
這世上的一切教法都可被包含在這個教法裡——無常。
思惟它,我已當比丘找了四十多年,也只找到這個——無常和安忍。
無常——一切都不確定,無論心多麼想要確定,只要告訴它:
「不確定!」每次心想執著某件事為確定的事物時,
只要說:「它不確定,它是短暫的。」
只要以這想法去降伏它,使用佛陀的「法」,回歸到這點上。
無論行、住、坐、臥,你都如此看每件事,
無論喜歡或不喜歡,都已同樣的方式看它。
這便是趨近佛、趨近「法」。
這是個值得練習的方式,我從過去到現在,都是如此修行。
我既不依賴經典,也不漠視它們;我既不依賴老師,也不「獨來獨往」。
我的修行一直都是「既非此,又非彼」。
這是件關於「滅」的事,亦即修行到終點站,
看見修行完成;看見表像,同時也看見超越。
想超越痛苦 就得避開苦並趨向佛陀
若你們持續修行,且徹底思惟,最後一定會到達這一點。
起初,你們匆匆前進,匆匆回頭,又匆匆停止。
你們持續如此修行,一直到往前、退後或停止都不對時,那就對了!
這就是結束,不要期待任何會超越於此的事;它就在這裡結束。
「漏盡者」(khinasavo)——完成者,他既不往前,
也不退後或停止,沒有停止、前進或後退,一切都結束了。
思惟這點,在心裡清楚地瞭解它,你會發現在那裡真的什麼都沒有。
這件事對你來說是舊或新,完全取決於你,
取決於你的智慧與洞察力,沒有智慧或洞察力的人將無法理解它。
只要看看芒果或波羅蜜果樹,若它們是許多棵一起成長,
其中一棵可能會先長大,然後其它的樹就會彎曲,向大樹之外發展。
誰教它們這麼做?這是它們的本質。
本質有好有壞,有對有錯,它能向正確傾斜,也能向錯誤傾斜。
不論什麼樹,若我們種得太密,
比較晚成熟的樹就會向大樹之外彎曲發展。這就是本質,或「法」。
同樣地,渴愛導致痛苦。
若思惟它,它就會帶領我們走出渴愛。
藉由觀察渴愛,我們重新改造它,讓它逐漸減輕,只到完全消失為止。
樹也是如此,有人命令它們如何成長嗎?
它們無法說話或移動,但知道避開障礙去成長。
只要哪裡擁擠,它們就向外彎,避開它。
「法」就在這裡,敏銳的人會看見它。
樹木天生就不知道任何事,它們是依照自然的法則在行動,
卻相當清楚如何避開危險,彎向合適的方向生長。
省察的人也是如此,因為想超越痛苦,我們選擇出家生活。
是什麼讓我們痛苦?若向內追蹤,就會找到答案。
那些我們喜歡和不喜歡的事物,都是苦的。
若它們是苦的,就別靠近。你想和因緣法談戀愛或憎恨它們嗎?
它們都是不確定的。當我們避開苦,傾向佛陀時,這一切都會結束。
無論聽見或看見什麼 都只能說:「這並不確定」
我是在一座普通的鄉下寺院出家,並在那裡住了好幾年。
在心裡懷著欲望修行,我想精通、想訓練。
在那些寺院裡,沒有任何人給我任何教導,但修行的想法就是如此生起。
我四處行腳參訪,以耳朵聽,以眼睛看。
無論聽到人們說什麼,都告訴自己:「不確定!」
無論看見什麼,我都告訴自己:「不確定!」
甚至當聞到香氣時,我也告訴自己:「不確定!」
或當舌頭嘗到酸、甜、鹹,以及美味與不美味時;
或身體感受到舒適或疼痛時,都會告訴自己:
「這並不確定!」我就是這樣與「法」同住。
事實上,一切都是不確定的,但我們的渴愛卻希望事情是確定的。
我們能怎麼做?一定要忍耐,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能忍辱。
有時我會去看有古寺建築的宗教遺跡,它們都是名師巧匠所設計與建造。
有些地方殘破不堪,我的朋友就說:「真遺憾啊!不是嗎?它毀壞了。」
我回答他:「若不是這樣,就不會有『佛』與『法』這些事了!
它會如此毀壞,是因為它完全遵從佛陀的教導。」
在我的內心深處,看到那些建築物毀壞我很傷心,
但我拋開感傷,嘗試對朋友和我自己說一些有用的話。
「若它不是這樣毀壞,就不會有任何佛陀!」
也許我的朋友並未在聽,但是我有,這是個非常、非常有用的思惟方法。
假設有人匆匆跑來,說:「隆波!你知道這些關於你的傳言嗎?」
或「他說你如何如何……」也許你便開始生氣。
你聽到一些批評,便準備要攤牌!情緒生起。
我們要清楚覺知這些心情的每一步,我們可能要準備報復,
但在看清楚事件的實相後,可能會發現他們所說的或指稱的是別的意思。
因此,這是另一個不確定的例子。我們為何要倉促地相信任何事呢?
為何要那麼相信別人的話?無論我們聽到什麼,
都應該注意,要有耐心,小心地觀察那件事。
任何語言若忽視這不確定,就不是聖者之言。
每次錯過不確定性,就會失去智慧,也偏離修行。
無論我們看到或聽到什麼,無論它是令人愉快或悲傷的,都只要說:
「這並不確定!」堅定地對自己如此說。
以此觀點看每件事,不要堆砌與擴大事端,
將它們都如此簡化,這裡就是煩惱滅亡之處。
若拋開聖者、佛陀或「法」 修行將變得貧乏且無益
若我們如此瞭解事物的真實本質,貪欲、迷戀與執著都會消失。
它們為何會消失?因為我們瞭解,我們知道。
我們從無知轉變成瞭解,,瞭解是從無知出生,
知道是從不知道出生,清淨是從污染出生,事情就是如此。
別拋開無常、佛陀——這就是「佛陀還活著」的意思。
佛陀已入滅的說法,不必然是真的,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它還活著。
這有如我們定義「比丘」一詞,若定義為「乞士」④,
意義就很廣泛。我們可如此定義它,但太常使用此定義並不是很好——
不知何時停止乞求!以更深刻的方式來定義,比丘可說是「看見輪回過患的人」。
這是否更深刻呢?「法」的修行就是如此。
當未充分瞭解「法」時,它是一回事;
但當完全瞭解時,它就變成另外一回事。它變成無價的,變成平靜的泉源。
當擁有正念時,我們就是趨近於「法」。
若有正念,就能看見一切事物的無常性,將看見佛陀,
並超越輪回的痛苦,若非於現在,就是未來的某個時刻。
若拋開聖者、佛陀或「法」,我們的修行就會變得貧乏與無益。
無論是在工作、坐著或躺著,我們一定要保持修行。
當眼見色、耳聞聲、舌嘗味,或身覺觸時——
在一切事情中,都別拋棄佛,別離開佛。
這就成為經常趨近佛陀與崇拜佛陀的人。
我們有崇敬佛陀的儀式,如在早上唱頌araham samma sambuddho bhagava
(應供、正等正覺、世尊),這是崇敬佛陀的一種方式,
但並非用前述的深刻方式崇敬佛陀。
只以巴厘語崇敬佛陀,就如同將比丘定義為「乞士」。
若我們趨近無常、苦、無我——
每次眼見色、耳聞聲、鼻嗅香、舌嘗味、身覺觸、意知法塵時,
那就如將比丘定義為「看見生死輪回的過患者」,
那要深刻多了,並斬斷許多枝節。
這就稱為「行道」,在修行中培養這種態度,你就是站在正道上。
若如此思惟與省察,即使可能與老師相隔遙遠,但仍會和他們很親近。
若和老師雖然比鄰而居,但心卻和他們沒有交集,
則你們只會將時間花在挑剔或奉承他們上。
若他們做了些你們合意的事,你們就會說他們很好;
若做了不喜歡的事,你們就會說他們很糟——
那將會限制你們的修行發展。
你們無法因觀察別人而獲得任何成就,
但若瞭解這個教法,當下就能成為聖者。
「法」並不能藉由順從欲望而達到
對於新進的比丘,我已訂下寺院的作息表與規矩,
例如「別說太多話」,別違背現有的標準,那是能達覺悟、證果與涅槃的道路。
凡是違背這些標準的人,就不是真正的、具備清淨動機的修行人。
這種人能見到什麼呢?即使他們每天都離我很近,他們也看不到佛陀。
因此,了知「法」或見「法」得依靠修行,要具備信心,並淨化自己的心。
若憤怒或厭惡的情緒生起,只要將它們放在心裡,看清楚它們!
持續觀察那些事,只要還有東西在那裡,就表示還得繼續挖掘與下功夫。
有些人說:「我無法切斷它,我辦不到!」
若我們開始如此地說話,
則這裡將只會有一群無用的傻瓜,因為沒有人斬斷他們的煩惱。
你們一定要嘗試,若還無法切斷它,就再挖深一點。
挖掘煩惱,再將它們連根拔除,
即使它們看來好像很堅實與牢固,也要挖出來。
「法」不是能藉由順從欲望而達到的東西,
你們的心可能在一邊,而實相卻在另外一邊。
你們必須注意前面,也要留心後面,那便是我說的:
「一切都不確定,都是短暫的」。
這個「不確定」的實相——
簡潔的實相,如此深刻與無瑕,人們卻對它一無所知。
不執著善,也不執著惡,修行是為了出離世間,將這些事做個了結。
佛陀教導要放下它們、捨棄它們,因為它們只會造成痛苦。
「注釋」
①別解脫戒(patimokkha):比丘所受持的戒律,每半個月便以巴厘語讚頌一次。
②波羅夷(parajika)或譯為「斷頭罪」、「驅擯罪」,
比丘有四條,是僧伽的根本重罪,犯者立刻逐出僧團。
僧殘戒(sanghadisesa),或譯「僧伽婆屍沙」,犯此戒者,
由最初的舉罪到最後的出罪,都必須由二十位僧伽決定,而可「殘留」在僧團中。
③阿那含:於斯陀含之後,再斷除嗔恚、貪欲二種煩惱,
至此階段完全斷除欲界的煩惱,不再生於欲界,
必定生於色界或無色界,在此獲得最高證悟,
或從欲界命終時,直接證得阿羅漢果。
④比丘(bhikkhu)原語系由「乞求」(bhiks)一詞而來,
即指依靠別人的施捨維生者。